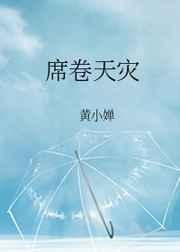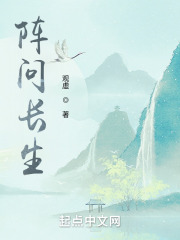1.3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历史转折
spanclass="xx1"1.3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历史转折/span
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它标志着赞成离开极“左”路线、开辟新道路的力量在执政党内取得了优势。
在粉碎“四人帮”和打开国门以后,人们比较中国和别的国家的发展情况,发现事实完全不像多年来的宣传教育所说,除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国家“风景这边独好”外,其他国家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许多人都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感触。这种感触推动了干部和群众对旧路线和旧体制反思和对其他国家的经验学习借鉴。虽然这些活动遭到部分坚持旧路线和旧体制的领导人按照“两个凡是”原则认定为“反对毛主席指示”、“损害毛主席形象”的“砍旗”行为而受到压制。但是,历史潮流是遏止不了的。变革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已经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两种不同的思想路线在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并以“凡是派”的失败告终。
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原定的议题,一是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是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总结讲话。
但是在会议的讨论中很快突破了这三项议题,把它开成了一次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确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会议,一度附和“凡是派”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这就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中国的历史大转变揭幕做好了准备。
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要解放思想。他说:目前在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少人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由于“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很多怪现象就产生了”。在这种情况下,“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党和国家“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因此,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针对过去“离开民主讲集中”,“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的情况,邓小平着重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
邓小平号召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在经济政策上,邓小平主张大胆下放过分集中的管理权力,以便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他提出了“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一“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因为,“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影响和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宣布“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终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对党内外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等口号,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路线的历史性转变。虽然极“左”理论和路线的影响仍将长期存在,但从执政党的决定而言,就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科斯(RonaldCoase)所感到的那样,这意味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正式划上了句号。
公报直接涉及改革具体措施的文字并不多,甚至完全没有提及后来成为改革主要内容的市场取向经济改革,但是它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要求全党“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样,就解除了思想桎梏,为人们认真反思过去的失误,探寻振兴中华的正确道路打开了闸门。
在改革初期,鉴于救亡图存的迫切性,中国领导人在进行改革理论和政策讨论的同时,采取了所谓“摸着石头过河”、“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策略:一方面,容许和鼓励地方政府进行体制和政策的调整,以便给予企业和个人发挥积极性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也在原有体制和政策的基础上做出一些变通性的安排,为民间创新创业活动开拓出一定的空间。
重要的变通性体制和政策安排包括以下各项:
第一,在土地仍归集体所有的条件下,以“包产到户”的形式让农民在从集体“包”(租)来的土地上实行家庭经营。
在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全国绝大多数农民都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强制下加入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个体农民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分得的土地也合并为“不可分割的集体财产”。1958年7月,毛泽东又号召把高级社合并组成“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土地、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资料都归“政社合一”的公社统一调配。这样,除国家不包工资分配外,“集体经济”已经与国营企业没有太大的区别。
在实现“合作化”和“公社化”以后,农民仍然希望重建自己的家庭经济。于是,一有风吹草动,比如说,遇到了荒年,他们就会在“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名义下提出承包土地、独立经营的要求。但是毛泽东把“包产到户”和集体农民拥有的小块“自留地”、农民出售家庭产品的“自由市场”以及个体工商业户“自负盈亏”放在一起,合称为“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每一次包产到户的要求都受到严厉的批判和制止。
“文革”结束以后,许多地区的农民再次提出实行包产的要求。后来通称为“包产到户”的包产责任制,当时有“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两种主要形式。前者与工厂中的计件工资相类似。它的基本做法是将各田块的产量指标分配给负责耕作的农户,在收获以后,由集体按各个农户包产指标的完成情况对它们进行分配。“包干到户”的基本做法是:作为土地所有者的集体(一般由村委会代表)按人口或按劳动力将土地发包给农户经营,农户按承包合同完成国家税收、统购或合同定购任务,并向生产队上缴一定数量留存用作公积金和公益金,余下的产品全部归农民所有和支配,从而取消了生产队统一经营和统一分配,“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因此,“包干到户”虽然还保留着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但在农业经营方式上已经实现了从集体经营向家庭在承包来的土地上经营的根本转变。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本站只支持手机浏览器访问,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
新起点小说【xqdxs2.com】第一时间更新《中国经济改革进程》最新章节。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
相关小说
- 入骨温柔
- 1.沈雁笙一直以为自己不喜欢陆景策,直到有一天听人家说,某集团大佬有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陆景策,她当天晚上气得饭都吃不下,回房就锁了门。晚上陆景策回来,从书房拿了钥匙,开门进她卧室,坐到床边,俯身把她从睡梦中吻醒。她没好气地看他,他却笑得愉快,还好意思问:“吃醋?”2.沈雁笙和陆景策一直地下恋,主要是她还没想好怎么跟爸妈解释他们俩的关系,导致她爸妈一直以为她单身,擅自做主骗她去相亲。偏偏某人那天正好
- 31万字一年以前
- 带枪出巡
- 男男现代正剧年下受腹黑攻【严楚x姜词】【双性生子产乳】1V1大概就是一个身为特警队长一直告诉自己我要矜持我得端着不行我不能沦落的双性冰山受被他家“小警员”捅到边哭边发浪一次又一次被干大肚子操到奶水四溢的故事。
- 29万字一年以前
- 小玲建军
- 丈夫常年在外,寂寞儿媳和公公同一屋檐下,一场情感纠葛,伦理大戏。…
- 9万字一年以前
- 怎敌她软玉温香
- 提起乔沅,上京诸人无不羡慕她的好命。出生钟鸣鼎食之家,才貌都是拔尖儿,嫁的男人是大霁最有权势的侯爷,眼见一辈子都要在锦绣窝里打滚。乔沅也是这么认为的,直到她做了个梦。梦里她被下降头似的爱上了一个野男人,抛夫弃子,为他洗手作羹汤,结果还被抛弃,最后在一个大冬天投了湖。梦的结尾,一个看不清面容的女人站在她的坟茔前,怜悯道:“夫人,你放心去吧,我会替你照顾好侯爷。至于小少爷,我找了一户人家,虽然以后不再
- 40万字一年以前
- 席卷天灾
- 预收1:带着超市大逃亡重生回来的乔青青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让丈夫回家。“请不了假?那你就跟老板说你老婆要跳楼了!”她冷静地开始网上购物,约师傅上门来改装门窗、加装水箱、安装太阳能,铺地暖……直到各种物资堆满家中每一寸土地,丈夫风尘仆仆出现在眼前,乔青青才大哭着扑上去“我好想你!”十年了,在那风雨交加,浮萍飘零的日子里,我每一天都在想念你。这一次我们要一起面对席卷而来的末世天灾,就算死也要死在一起
- 104万字一年以前
- 阵问长生
- 修界九州,道廷一统,世家压迫,宗门垄断,修道壁垒森严。底层修士修道无门,灵石匮乏,度日维艰。十岁的墨画,先天体弱,散修出身,家境贫寒。即便苦心修炼,终其一生,可能也只是一个卑微如蝼蚁的炼气修士。直到他的识海中,出现了一块道碑。可以领悟天道阵法,无限增强神识。墨画将借道碑,破碎修道壁垒,铸就无上神识,彻悟仙道阵法,问鼎长生大道……
- 31万字一年以前